- 政策解读
- 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减贫救灾
- 法治中国
- 天下人物
- 发展报告
- 项目中心
莫理循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关键词: 泰晤士报 袁世凯 朱尔典 丁家立 旁观者 公共关系 协约国 北京的莫理循 二十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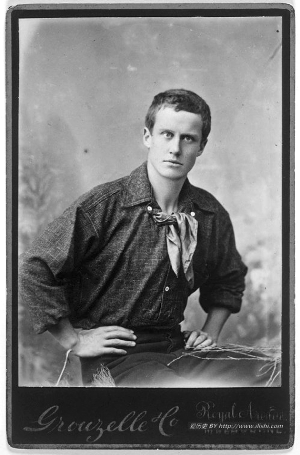
莫理循(1862-1920)
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
我叫莫理循,澳大利亚人,从事新闻工作。今年是1911年,我在王府井大街100号已经住了9年。正如你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辛亥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在北京,我的人脉关系网使我的报道总是领先于其他报纸,新闻界给我很高的评价。中国有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辛亥革命,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随后的一年,我受聘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也就是袁世凯顾问,我的爱情苦尽甘来,我与珍妮小姐结为夫妻。事业有成,婚姻幸福,人生圆满,不是吗?
“旁观者清”
推袁,只是顺水推舟
辛亥革命爆发那天,我去拜访了赫德的接班人、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据此写好了新闻稿:“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已经使北京陷于极度惊慌之中……”电报传到《泰晤士报》,引起英国舆论的极大关注。
从10月11日至11月24日,我总共发给《泰晤士报》8113个字的电文。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的信息来源既有丁家立、青木宣纯等美日外交官等等,也有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及唐绍仪、梁士诒、汪精卫等人,这些报道的准确性与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来得太突然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辛亥革命前,我曾写信给严复先生,询问关于中国政局的问题,严复先生用古雅的英文给我回信说,中国应当先搞君主立宪,再过30年搞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共和制比较合适。实际上我比较认同严复的观点,对中国政局,我也倾向君主立宪。
但革命爆发没多久,我就知道我与严复先生都错了。
11月16日,蔡廷干到我家,长谈了好几个小时。他告诉我,君主立宪已经没有可能,皇室也已意识到处境艰难。
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在北京的革命党希望我去汉口。英国公使表示赞成,袁世凯也希望我去,并为我准备了专车。这个使命,我很乐意接受,我先到汉口,然后又去了上海和南京。
在上海,我与许多革命党人见面,指出列强不可能承认孙文或黎元洪,而属意于袁世凯。我的游说起到了一定效果:革命党领袖对我说,他们肯定会同意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唐绍仪曾经设想,召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这样可以使袁世凯不用被人指责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
1912年1月5日,我去见袁世凯。袁小声对我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1月10日,蔡廷干写信给我,希望我动员上海商会领头请愿,要求皇帝退位。我给上海工部局卜禄士写信提出,请上海商会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说皇室妨碍和平,请皇帝退位。如果上海商会这样做了,其他商会也会这样做,联合起来,力量将会很大。因此,香港、上海的商会都发出了通电。
1月16日,我和罗宾小姐站在王府井大街的寓所门前,等待袁世凯的马车通过,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几名革命党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失败了。
不过,很快袁世凯似乎就胜利了。2月12日清帝的退位诏书中讲:“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自然,我也率先独家发表了清帝即将退位的新闻。
作为《泰晤士报》记者,一个中国政局“旁观者”,对袁世凯的相助,只是锦上添花。我很清楚,这一年,袁世凯纵横捭阖,谋得总统之位的真正原因,是他在中国毋庸置疑的实力。
“当局者迷”
顾问,“看上去很美”
中国的事情,在1912年年初,似乎看起来已经结束了。皇帝退位,革命党人得到了共和,袁世凯也做了总统。1912年,对我个人来说,私事是,要正式确定与珍妮·罗宾小姐的关系。另一件事情,可能烦恼得多,是关于中国政府顾问这一角色。
毕竟我已经50岁了,滑膜炎使我的疾病复杂化。出乎意料的是,我招募的秘书珍妮·罗宾,我也越来越被她的女性魅力所倾倒。在1912年4月晴朗宜人的一天,当我和她在宽敞的城墙上散步时,我吐露了对她的爱慕之情。但我比她大27岁,她家里人是否同意?应珍妮的要求,我给她父亲写信求婚。
我曾接到蔡廷干的一封信,请我做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他在1912年8月2日证实了对我的任命。就在这段时间,我也接到了岳父同意这桩婚事的来信。8月19日,我回到了伦敦,四处游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为袁世凯处理“公共关系”,而且卓有成效。人们都对我的新职表示祝贺,陆军中将那德·波尔·卡鲁爵士等人,让我帮助找工作。还有很多人,想让我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许多人要求会面,也让我应接不暇。在英格兰南部的南克洛顿,我与珍妮完婚。第二天,我和她在早餐前漫步了14英里,在户外的池塘边吃了午饭。
圆满的婚姻、可观的薪水、世界性的声誉,似乎很令人陶醉。但我很快发现,与做《泰晤士报》记者相比,作为中国政府的参谋,我实际上是个摆设,能够做的事实在有限。北京的政客们,腐败、堕落,充斥着阴谋与谎言。没做多少事而享受高薪,并得到袁颁发的“二等嘉禾勋章”,我受之有愧。
在上海时,我曾经对澳大利亚人,《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说,你为什么不到革命政府任职?端纳说,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我知道,端纳是对的。
当时,有关贷款和租界,鸦片和铁路,西藏和蒙古等问题的争论无止无休。我为此殚精竭虑,提供了许多咨询文件。即使建议不被重视,我也照提不误。宋教仁被暗杀后,国务总理赵秉钧委任我和伍廷芳对宋案详尽调查具报。我此前对于中国政府七拼八凑的有关宋案的解释满腹狐疑,当即拒绝。
对于我推举的袁世凯,我看到了他以暗杀、恫吓和贿赂为政治武器。但是,我做中国政府顾问,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915年,我与好友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披露给《泰晤士报》,将日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我还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我这个顾问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文虚拟莫理循自述,参考了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北京的莫理循》、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中国的莫理循》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