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围绕目前中国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有哪些难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如何评价中国生态环境发展历程?就这些热点话题,记者专访了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吕永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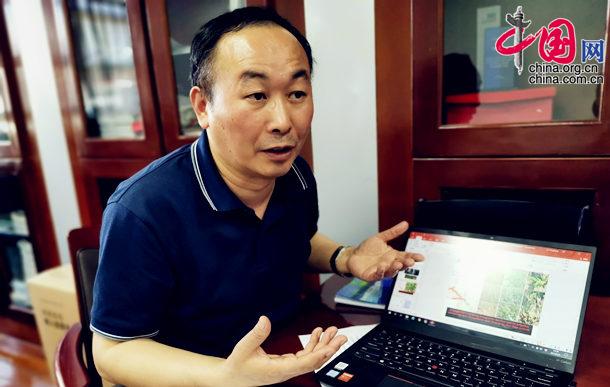
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吕永龙。
源头控制当务之急,应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记者: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您认为目前中国污染防治的难点是什么?
吕永龙:对中国来讲,最大的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的难点是多种污染物并存、多种污染源并发、多种环境介质受到影响,污染不仅造成生态环境风险,也通过呼吸、接触或食物链/网的传输过程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威胁。不是单一的污染物产生的污染问题,而是多种种污染物在环境中并存,通过相互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形成复合污染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污染物在多种介质间传输,以及多种污染源并发。多种介质包括大气、土壤、水、生物等,这些污染物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而是通过传输和扩散的过程,在多种介质中都存在。多种污染源并发,不仅有点源问题,还有面源问题。
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要找到污染物的源头在哪儿,到哪儿去,影响的范围和损失多大,以及形成的原因,都成了污染防治攻坚的难点。
比如说,有的大气污染,其实不完全是大气污染。污染物经过大气传输过程,沉降到地面,就会给土壤、水带来污染。我们强调综合性的污染防治,而不是单纯地将水、土等环境介质割裂开来,我不太赞成水污染就治水,气污染就治气。土壤污染之所以很复杂,是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壤问题,很多情况是大气沉降、水传输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记者:那么,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今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吕永龙:当务之急是抓好源头控制,这不是新观念,发达国家早就提出来从源头的预防性举措。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产业发展问题。难点在哪儿?一方面要追求经济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一个清洁的环境,这就需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产业结构,这是个大问题。
污染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并不是中国现在特有的问题,发达国家在20世纪就已经发现这样的问题。2017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整理的最经典文章中有一篇1922年发表的论文,就是关于美国工业污染所引起的生态问题。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关注的环境冲突,都是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
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对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我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有发展阶段性的因素。发展初期,有人为了经济效益不择手段,或者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余地,会选择一些已经淘汰的落后技术和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发展起来的,为什么选淘汰的产业?这是因为虽然污染相对比较重,但是成本低,在全球范围内仍有需求。
除了产业发展之外,还有就是要转变生活方式。如今生活所产生的污染物越来越多,而且生活的污染排放过程不像工业,工业污染排放固定的点污染源多一些,生活源污染面广、量大。尤其与行为方式都有关系,比如,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控制塑料的使用,2017年肯尼亚施行全球最严禁塑令,在肯尼亚生产、销售或使用塑料袋将面临1—4年的监禁或最高400万肯先令(约合人民币26万元)的罚款。除了塑料污染,化妆品、一般生活用的化工品,都存在新型污染物的问题,这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不仅对生态系统,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有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可能在某个时段变成了污染物。这是因为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后,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提升了。再加上随着一些高精尖的技术手段出来,发现新型污染物的水平和能力也提升了,过去很难发现和检测到的污染物,现在可以检测出来了。比如,过去我们认为电子产品没有污染,现在证明不但有,而且很多是属于持久性的有毒污染物。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的东西,新的化学合成产品,看似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没什么影响,但是要想真正弄清楚是否有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要强调一点,在中国现阶段,污染源防控与污染控制两方面要并举。对中国来讲,现在光从源头防控是不够的,因为很多是过去积累的污染问题,现在必须要控制和消除这类污染,对目前的污染场地或区域要进行生态修复,提升其生态服务功能。目前大量的精力或者投入主要放在污染控制上面,我们也在想办法从源头上来预防。
摸清污染源家底,来去有“数”
记者:您一直强调源头控制,然而,确定污染物的来源与去向一直是困扰中国科研工作者多年的难点。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吕永龙:这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做污染物的源解析,污染源的辨识问题。污染源的识别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产业,或从工业发展过程来看有哪些工业部门,哪些具体的行业,对这类的污染贡献比较大,要找到这一类的产业。另一方面,我们要从环境中大规模采样分析,尤其是区域性采样,采用环境地学方法进行系统采样,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有序列性,比如有时间序列,了解整体污染物在介质中间的降解情况,获取比较长时间序列的数据。

沉积物采集器安装与前期准备
一般来讲,在一个样点采样要坚持很长时间。每隔几年,或者五年,再大范围进行一次采样,看一下这种污染物在这个时间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经过分析之后,可能选择重点的研究区域进行重点采样,要采水、土、生物、大气各种各样的样本。到实验室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了解环境介质(水、土、沉积物)里面的污染物的化学结构是什么样的,再对比分析生产企业生产的化学产品结构,分析到底哪些行业是有贡献的。

水体样品采集

湿地分层样品采集

浅水湖泊沉积物样品采集

农田土壤样品采集

河流沉积物样品采集
另外,从历史来看,我们采用采集定深沉积物方法,分析污染物可能在环境介质中到底存续了多长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产业生产的产品与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通过化学结构分析和年代溯源后,可以找出来哪些行业哪些企业对这一类污染贡献最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做行业排放因子分析,并根据产品生产量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估算。
刚才讲到的生活污染源也是非常重要的源,每个人都有贡献。这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人口,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富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需要估算每年的排放,尤其对于城市来讲,都是生活污染主要通过污染物集中处理系统对外排放,所以,通过污水集中处理系统的流量可以作为生活污染排放量的重要估算依据。由此可以获得这两类源各自贡献到底有多大,全部估算完之后,就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出其分布特征。
环境风险图谱预警产业结构调整
记者:您这项研究是把整个水、土、食品、健康和环境整个做了一个协调联动的链条,目前,这项研究有没有运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以此指导地方或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可持续发展呢?
吕永龙:有。我们在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过程中,要明确污染到底对当地有哪些影响,影响范围有多大,产生了多大的损失等。比如,北京周边曾经是种水稻的地方,但随着一些工业沿河道布局,河流受到了污染。当地农民种小麦、水稻、大豆、玉米之类的农作物,一直用河流的污水进行灌溉,致使离河道越近的作物收成越低,甚至颗粒无收。这类污染事件也是社会不稳定之源之一,因此,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帮助分析灌溉河流的污染物、农田生态系统的污染状况,找出造成损失的原因,给出建议,指导地方政府和农民采取必要的对策。
污染物找到之后,顺着找源头,找产业。往往造成污染的产业对当地来讲都是经济支柱甚至是地方税收的重要部门,所以我们做科研要为当地解决问题,了解污染状况及其根源,给政府提供决策支持。
另外,我们也会到车间对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采样,分析哪些环节是最重要的排放源,哪些车间排放量比较大,从生产物料平衡的角度去做分析,给政府作参考,指导企业改进生产工序。
这些数据分析对地方政府和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过科学的分析知道哪些产业要优先发展,哪些要制约。
记者:您的这种做法是给地方和企业绘制了一个环境风险图谱,按照这个图谱进行预警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成果将来会大范围推广应用吗?
吕永龙: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控制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对所有的污染物都控制?我认为不需要全部控制,应该根据当地的保护目标来选择优先控制的污染物。在许多污染物并存的情况下,到底选哪些污染物优先进行控制,我们对不同保护对象的污染物风险进行了排序。风险越大就把它作为重点的控制对象,在重点区域进行优先控制。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污染物生态风险图做出来,在控制的时候根据确定保护的目标来进行选择。比如一个地方要保护的是一种鸟类,那就要以这种鸟类作为保护对象,它对什么样的污染物最敏感,就优先进行控制,要分清轻重缓急。
渐进式变革的发展道路适合中国国情
记者:这样做有的放矢,既能根据实际情况保护环境,又能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的环境状况一直因发展变化,从先发展后治理到边发展边治理,到目前的以恢复保护为主的生态环境发展观,您如何评价这样的发展?
吕永龙: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发达国家讲“你们在走我们20世纪发展的老路,我们都已经污染过了,你不能再污染。”还有人提出跳跃式发展,跳跃式发展有陷阱,我并不完全赞成。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的工业体系没有那么先进,技术员、高级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等各方面都缺乏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跳跃式发展?只能逐步发展。任何发展都要量力而行,我认为中国发展走的路是对的,选择的是渐进式变革的发展道路,适宜的技术,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现在很多污染问题,跟上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有关。当年很多地方都强调沿着河岸布局小纺织、小机械、小造纸等等,那时候人们认为冒烟就是好的,冒烟代表是有技术的,因为不了解发展过程。如今社会逐步发展了,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有的人说希望回到以前,但是回到以前那是一个原始的生活状态,跟国际水平是不可比的。人们向往生活在没有城乡差别,过着富裕生活但又没有污染的地区。
当前我国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持续地支持一些科研机构,做系统性研究,注重数据资源的积累与储备,加强生态系统保育和环境技术创新。不能再走发展低端产业的老路,要从污染源头上控制,把好关。我国已经跨越了技术、人才、经验储备和积累的阶段,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可持续的产业,这不是简单的GDP增长,而是生态资本也能增加,至少是保护生态的,这是极为重要的。
不要认为过去的发展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没有过去的经历与经验,老百姓也不会认识到现在的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还在为解决温饱而奋斗,没有能力去顾及到环境问题。如今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群众的环境意识也在逐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变得更为紧迫。
记者:能理解成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吗?
吕永龙:对,如果说必然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赞同,但是确确实实是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也培养了人的环保意识。我讲一个案例,中国人对于核辐射污染的认识,最大的一次震动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对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没有什么感觉,实际上这两次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更惨痛。一是因为日本距离我们很近,二是2011年中国人已经开始关注环境、自己的安全和健康,这绝对是发展阶段性的问题,需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是解决新型环境问题最好的实验场
记者:科研的进步和领先能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预见性的指导,那么,中国在污染防治的研究中,与国际水平相比处在怎样的水平?
吕永龙:从时间上看,我们是有差距的。因为20世纪发达国家就遇到了很多的污染问题,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了。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他们曾不同程度地遇到,为什么说不同程度呢?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污染问题比他们更复杂,比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60年代的洛杉矶雾霾污染事件,这都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的雾霾天气滞后他们多少年?所以发达国家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对于规律的认识,研究手段和方法,特别是在一些学科的发展上,肯定是由他们发起的。比如,现在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环境地学的研究,开山鼻祖以及走在前沿的,都是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他们是这些学科的先驱者,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找到解决方法,研究新的理论。近些年,中国在地学、环境、生态学领域发展快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非常活跃,现在和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已经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而是一个对等的合作关系。为什么是对等合作?第一,我们现在运用的方法、手段,包括根据实际问题产生理论等方面,是可以走在前沿的。为什么能走在前沿?解决新型的环境地学和生态学问题,中国是最好的实验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好。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也很大,发展阶段也很不同,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地学的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找到。
我的团队跟英国研究机构合作比较多,英国现在污染没有那么严重,研究人员强调的是能不能把英国的科学和技术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在寻找他们的科技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环境问题,我和他们说要改变一下思路,不是所有都强调是英国的科技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应用,还要考虑中国新的理论方法在英国的应用。
我们与欧洲这些国家的差别在于,他们很多研究是非常系统性的,强调科学和政策的结合,科技成果怎么样运用,而我们有欠缺。我们很多环境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属于舶来品,我们如何做系统的研究,掌握系统的数据,在现阶段非常重要,只有更科学的数据才能反映生产生活带来的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记者王振红 特约记者杨柳春)